
“卡点”入股、套现数亿!审计署披露江苏证监局原局长贪腐细节


独家抢先看
6月24日,审计署在官网发布《国务院关于202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》。报告披露,2024年5月以来,审计共发现并移送重大违纪违法问题430多起,涉及1400多人、630多亿元。
其中,一起涉及金融监管系统内部人员的腐败案件引发关注。
《报告》指出,一省证监局原局长凌某等人 2011 年以来,伙同3 户企业实控人,先在上市前借用亲属账户“卡点”突击入股,并采取银行票据背书转让等非现金、非常规转账方式隐匿入股资金来源,再在上市中为3户企业提供辅导备案、上市保荐,上市后凌某等人将购买的原始股已累计减持套现数亿元,且获利资金长期存放他人账户,只在使用时才转入个人名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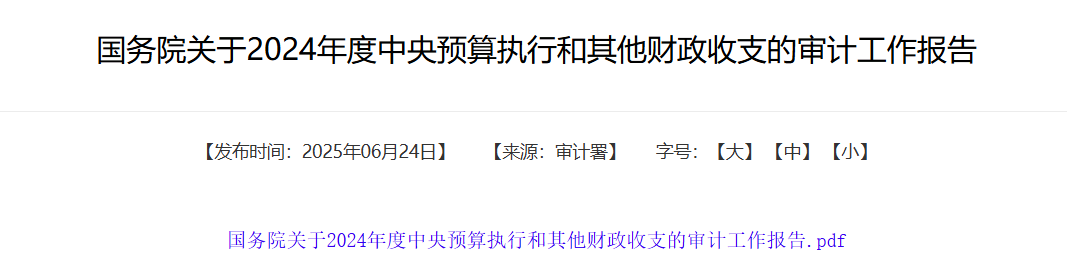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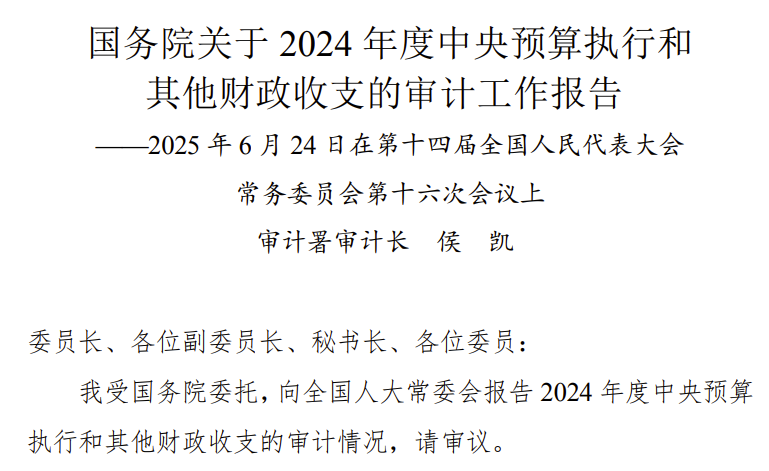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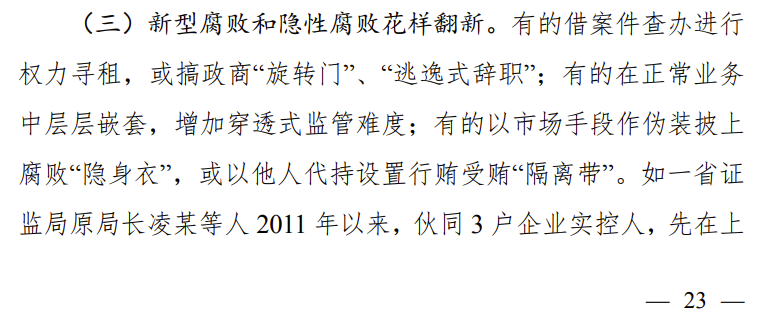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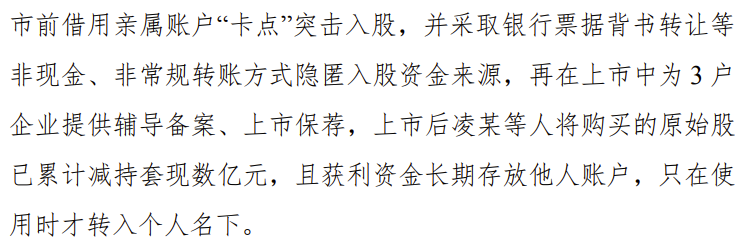
尽管审计署报告只指出“一省证监局原局长凌某”,未披露哪个证监局及全名,但根据中国证监会网站2024年12月27日发布《江苏证监局原党委书记、局长凌峰被开除党籍和公职》。江苏证监局局长凌峰违法事项之一为“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,将应当由本人支付的费用由他人支付;以“投资入股”名义非法收受财物,数额特别巨大等信息,基本可以认定国家审计署报告中的“一省证监局原局长凌某”即为江苏证监局原局长凌峰。

公开信息显示,凌峰,男,1972年生,安徽合肥人,1993年8月参加工作,在证监系统工作二十余年。
2004年至2020年,凌峰于江苏证监局任职,从江苏证监局期货监管处副处长起步,历任办公室主任、江苏证监局副局长。2020年外放贵州证监局任局长“镀金”后,2022年重回江苏,担任江苏证监局党委书记、局长。
2024年6月,江苏证监局原局长凌峰在任上被查,并在24年12月被双开,当时的通报称,其以监管者身份谋取私利,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,甚至以“投资入股”名义非法收受巨额财物。他还被指对抗组织审查,与多人串供,转移隐匿违法所得。江苏省纪委监委认为,凌峰的行为,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,且不知止不收手,性质严重,影响恶劣。经江苏省纪委监委研究,决定将凌峰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,所涉财物一并移送。
此次审计署的报告,再度揭开了凌峰案的“操作细节”,也进一步印证了此前“双开”通报的内容。
审计报告显示,凌峰等人的贪腐轨迹始于 2011 年,其核心手法是利用监管职权与企业实控人合谋,在企业上市前通过亲属账户突击入股。这种 “卡点” 操作具有极强的时间敏感性 —— 通常在企业申报上市材料的关键窗口期,借助信息优势精准布局。交易资金则通过银行票据背书转让等非现金、非常规转账方式流动,形成多层资金嵌套,刻意隐匿资金来源与实际控制关系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资金运作的隐蔽性。调查发现,涉案资金从未直接进入凌峰个人账户,而是长期存放于第三方托管账户,仅在使用时才通过多层转账进入特定消费场景。例如,2020 年凌峰在上海购置的一套价值 2800 万元的豪宅,其资金链可追溯至某贸易公司账户,而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正是涉案企业的关联方,整个资金链条经过 7 家空壳公司的周转,形成严密的 “防火墙”。这些资金长期滞留他人账户,仅在使用时零星转入个人户头,形成“资金寄生”生态。
在企业辅导阶段,凌峰利用对上市审核标准的掌握,指导企业 “精准” 调整财务数据,规避监管红线;在保荐环节,通过干预中介机构选聘,指定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券商担任主承销商;甚至在发审会前夕,通过泄露内部审核意见,帮助企业提前应对问询。企业上市后迅速减持,累计套现数亿元。这种操作本质上构建了一个闭环:监管权力为企业上市护航→企业出让原始股作为回报→监管者套现后继续寻租。
他这种“寄生账户”模式极具隐蔽性——资金平日沉睡在他人名下,既规避银行大额交易监控,又避免账户异常波动。待消费时蚂蚁搬家式转账,实现“脏钱体外循环,干净消费入账”。若非审计署穿透式追踪资金流向,他罗织的黑网或将继续笼罩江苏资本市场。
审计署在报告中特别指出,新型腐败和隐形腐败,有的借案件查办进行权力寻租,或搞政商“旋转门”、“逃逸式辞职”;有的在正常业务中层层嵌套,增加穿透式监管难度;有的以市场手段作伪装披上腐败“隐身衣”,或以他人代持设置行贿受贿“隔离带”。
凌峰案暴露的不仅是个人贪腐问题,更凸显了当前金融监管在应对复杂资本运作时的制度短板。反腐利剑已刺破黑幕,而制度重建的长路,才刚刚开始。







